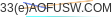庄子分节 19
【导读】
记住【奥福书屋】:AOFUSW.COM
本文选自《骈拇》篇,以“骈拇”与“枝指”为喻,刻地批判了社会
那些滥用智慧、矫饰仁义的行为,而倡扬
种“
失其
命之
”的自然正
。
阅读这篇文章,应当关注两点,是“
起”,作者以
的“骈枝”(多余的赘
)
起
事的“骈枝”(多余的行为),为行文展开了阔
的
间。二是首尾呼应,开篇以“骈枝”引发相关议论,戟指仁义之徒滥用
己之聪明,反而伤害了
命之
、
德之正的虚矫行径。由此宕开文
,作者批评的是“多骈旁枝之
”,而收束
复论“骈枝”,则转为“骈于拇者,决之则泣;枝于手者,龅之则啼”,所谓或多余,或
足,都是自然而生的应有之数(状),更
入地说明了无论是
之“骈枝”,抑或
世之仁义,都是自然属
,而无故为之用的
理。
由此“骈枝”引发的批判,在本文中又突表现在两方面:
方面是对“
”的奢
。对此,《老子》第十二章有段愤
之词:“五
令
目盲,五音令
耳聋,五味令
,驰骋田猎令
心发
,难得之货令
行妨。”其悦“目”之五
至于“盲”,悦“耳”之五音至于“聋”,悦“
”之五味至于“
”(败),强“
”之田猎至于“心发
”,珍美之“货”(
)至于“行妨”,这是老子否定中的疑问。而庄子在这里转换其义,以“离朱”之明为“
五
,
文章”,以“师旷”之聪为“
五声,
六律”,以“曾、史”之仁为“擢德塞
”,以“杨、墨”之辩为“无用之言”,此皆非天
“至正”,均在摒弃之列。
另方面是专就“仁义”发论,反复强调“意仁义其非
乎”,“故曰仁义非
乎”。因为在庄子看
,造作仁义并将其用于个
的修养和国家的治理,企图用仁义礼智信比同于
的五脏,是
懂仁义礼智信
本就
是
德的本然状
。换言之,骈拇、枝指是某些
天生
有,没有任何用
,亦非
之正、
能等同五脏看待,仁义礼智信如同骈枝,也只是为某些
天生
有,而
是
德的本
,
可片面地强调它们,并用以
化别
,治理国家,否则,会导致
僻
正的风气。所谓“凫胫虽短,续之则忧;鹤胫虽
,断之则悲”,顺适自然,有“骈枝”亦如无“骈枝”,“仁义”必符“
”,“
”本于“自然”,这才是庄子强调的“
命之
”与“至正”之
。唐文治《国文
义》认为:“有辩学而
有辩才,纵横机
,虽以无理之辞而若有至理寓乎其中,是谓辩才,如《庄子·骈拇篇》是也。”对照此文之辩才,可见庄子之辩在纵横机
的战国时代,允当自为
格。
夫小易方,
易
。[1]何以知其然
?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
也,天
莫
奔命于仁义,是非以仁义易其
与?[2]故尝试论之,自三代以
者,天
莫
以
易其
矣。[3]小
则以
殉利,士则以
殉名,
夫则以
殉家,圣
则以
殉天
。[4]故此数子者,事业
同,名声异号,其于伤
以
为殉,
也。[5]臧与谷,二
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。[6]问臧奚事,则挟□读书;问榖奚事,则博塞以游。[7]二
者,事业
同,其于亡羊均也。伯夷
名于首阳之
,盗跖
利于东陵之
,二
者,所
同,其于残生伤
均也,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![8]天
殉也。彼其所殉仁义也,则俗谓之君子;其所殉货财也,则俗谓之小
。其殉
也,则有君子焉,有小
焉;[9]若其残生损
,则盗跖亦伯夷已,又恶取君子小
于其间哉![10]
【注释】
[1]易:更。方:四方,方向。
:天
,自然的
分。[2]自:从,
说当作“有”,与
文“虞氏”连读。招:取,举。挠:扰
。是:这种
法。与:同“欤”。[3]以
易其
:以外
更其
分中
有的东西,即
文所谓以
殉利、名、家、天
。[4]小
:指普通的老百姓。
:
躯,这里
有生命、天
的意思。殉:营
,
说当解作“杀
从之”。圣
:指世俗所谓的圣明君主。[5]事业
同:指为名、为利、为家、为天
的
同。名声异号:指小
、士、
夫、圣
的称号
同。伤
:伤害天
,与“以
为殉”同义。[6]臧:好学的
,
说娶婢女的男子称为“臧”。榖:与“□”同,小孩。[7]□:与“策”同,古代用
书写的竹简,这里指代书籍。博塞:
种博弈游戏。[8]首阳:首阳山,在今山西永济境
。盗跖:
秋时候的
盗,传说为柳
惠的从
。东陵:泰山,
说是陵名。所
同:指伯夷是为名而
,盗跖是为利而
。[9]则:而。[10]残生损
:残害生命,损伤天
。已:与“矣”同。
【导读】
本文选自《骈拇》篇,承接文“自三代以
者,天
何其嚣嚣”发论,批评其“奔命于仁义”之途以致“残生损
”的危害,并举例明事,再阐
命之正与自然之
。
作者首以“小易方,
易
”开启笔锋,突
“
”字,引
文。追
寻源,庄子以为其“
”首在有虞氏“招仁义以挠天
,天
莫
奔命于仁义”,故而三代以
,皆以“
”易“
”。至此,作者以四排句徒起文
,即“小
殉利”、“士殉名”、“
夫殉家”、“圣
殉天
”,
“
”承
“殉”,点破了“伤
”的
源。由此,作者再以“两扇法”行文,先以“臧与谷”二
行为说事,
则读书而亡羊,
则博塞而亡羊,所谓“事业
同,亡羊均也”。再以“伯夷”与“盗跖”对比,
者殉名于首阳,
者殉利于东陵,所谓“所
同”,而“残生伤
均也”。所以从名利的层面看,有清浊是非之分,如果从自然
命的层面看,其“
”其“殉”,其“残生损
”是
样的,何
清浊是非之分呢?
这段文字,是庄子以齐
的视域探究
命之说,文简意赅,析理明辨。
☆、正文 第二章马蹄
伯乐治马
马,蹄可以践霜雪,毛可以御风寒,龅草饮,翘足而陆,此马之真
也。[1]虽有义台路寝,无所用之。[2]及至伯乐,曰:“
善治马。”[3]烧之,剔之,刻之,雒之,连之以羁□,编之以皂栈,马之
者十二三矣;[4]饥之,渴之,驰之,骤之,整之,齐之,
有橛饰之患,而
有鞭□之威,而马之
者已
半矣。[5]陶者曰:“
善治埴,圆者中规,方者中矩。”[6]匠
曰:“
善治木,曲者中钩,直者应绳。”夫埴木之
,岂
中规矩钩绳哉?然且世世称之曰“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”,此亦治天
者之
也。[7]
【注释】
[1]足:说当作“尾”。陆:跳跃。真
:自然的本
。[2]义:借为“巍”,
,
说与“仪”同。路寝:
殿。
[3]伯乐:秦穆公时,善相马,姓孙,名阳,字伯乐。
[4]烧:打烙印。剔:剪马毛。刻:削马蹄。雒(luò):笼头,
说当解作“打烙印”。羁□(zhí):絷,绊绳。皂栈:槽枥,马
。
[5]整、齐:指排布行列。橛(jué):马中的衔勒。饰:马镳
的装饰
。鞭□:即“鞭策”,赶马用的鞭子。
[6]陶者:制作陶器的工匠。埴(zhí):粘土。中:。[7]治天
者:即
文的“圣
”,指世俗所谓的圣明君主。
吾意善治天者
然。彼民有常
,织而
,耕而食,是谓同德;[1]
而
,命曰天放。[2]故至德之世,其行填填,其视颠颠。[3]当是时也,山无蹊隧,泽无舟梁;[4]万
群生,连属其乡;[5]
成群,草木遂
。是故
可系羁而游,
鹊之巢可攀援而窥。
夫至德之世,同与居,族与万
并,恶乎知君子小
哉![6]同乎无知,其德
离;[7]同乎无
,是谓素朴;[8]素朴而民
得矣。及至圣
,蹩躠为仁,踶跂为义,而天
始疑矣;[9]澶漫为乐,摘僻为礼,而天
始分矣。[10]故纯朴
残,孰为牺尊![11]
玉
毁,孰为珪璋![12]
德
废,安取仁义![13]
离,安用礼乐![10]五
,孰为文采!五声
,孰应六律!夫残朴以为器,工匠之罪也;毁
德以为仁义,圣
之
也。
【注释】
[1]德:,指自然的天
,
说与“得”同。同德:指万
顺
而行,都在自己的
分之
得到
足。
[2]:浑然
。
:偏。命:名。天:自然。天放:指顺应自然天
而自由自在的
种状
。
[3]至德之世:指没有遭到破
的纯朴时代。填填:稳重安和的样子。颠颠:专
的样子。[4]蹊:小径。隧:隧
。
[5]连属其乡:指万居住的地方,如同连在
起,形容万
适
自然,融洽而没有分别的样子。
[6]同与居:即“与
同居”的倒装,“同居”即共同相
的意思。族与万
并:即“与万
并族”的倒装,“并族”即同类的意思。
[7]此句言家都
用智巧,本
就
会远离。[8]素朴:纯真朴实,指天
没有受到损伤。此句言
家心中都没有贪
,这就
纯真朴实。[9]蹩躠(bié
xiè)、踶(zhì)跂:都指用心为仁义的样子。[10]澶(dàn)漫:放纵安逸的样子。摘僻:当作“摘擗”,烦的样子。
[11]纯朴:指树木的自然状。残:指雕刻。牺尊:即“牺樽”,指装饰有牺牛形象的酒杯。[12]珪璋:
尖
方的玉器
“珪”,“珪”的
半就
“璋”。
[13]德:指自然天
。[14]
:指万
所禀受的
分。
【导读】
本文选自《马蹄》篇,以“伯乐治马”说事,而讨论“善治天
”的
理。
自先秦史著记载秦穆公时“伯乐”善“相马”,此故事流传
,耳熟能详,皆以赏识
才者为“伯乐”,以致韩愈
叹:“世有伯乐然
有千里马,千里马常有而伯乐
常有。”(《杂说》)而庄子则
然,
开篇先明“马”之“真
”,即蹄践霜雪,毛御风寒,龅草饮
,翘足而陆的
状,而伯乐反以“烧之,剔之,刻之,雒之”,“饥之,渴之,驰之,骤之,齐之”诸法,致使马
半,而自谓“善治马”。同样的
理,陶者使“圆者中规,方者中矩”以为“善治埴”,匠
使“曲者中钩,直者应绳”以为“善治木”,皆戕害土、木之本
而适于己,
如伯乐戕害马的真
而为
所役使,都是
为的
错。
读《庄子》文章,常有笔法,所谓“难说之理能
笔达之,难达之意能
语明之”(章廷华《论文琐言》)。在这里,作者由伯乐治马、陶匠治埴木
笔跳
,直接承以“亦治天
之
”的
喟,以引起有关善治天
的讨论。而其“吾意善治天
者
然”
句,是承
启
,“
然”二字为转折,以扬弃伯乐治马之法,论治天
法。庄子所谓的善治天
,突
在“同德”之
与“至德”之世。这段文字又分为两层,
言因“同德”之民
观“至德”之世
的自然状
,
言破
了“至德”之世对“同德”之
的损伤。文中对“蹩躠为仁,踶跂为义”、“澶漫为乐,摘僻为礼”之圣
行为的提
,对“
德
废,安用仁义;
离,安用礼乐”的质疑,如同老子说的“
废,有仁义;智慧
,有
伪”(《老子》十八章),是由愤世意识而讨论治世思想的反映。
文章最以“残朴以为器,工匠之罪也;毁
德以为仁义,圣
之
也”的对排句收束,又将
面两段文字的“治马”与“治世”之论绾
,章法井然,而文旨明豁。
☆、正文 第三章胠箧
胠箧与窃国
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,则必摄缄縢,固扃鐍,此世俗之所谓知也。[1]然而巨盗至,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,唯恐缄縢扃鐍之固也。[2]然则乡之所谓知者,
乃为
盗积者也?[3]
故尝试论之,世俗之所谓知者,有为
盗积者乎?所谓圣者,有
为
盗守者乎?何以知其然
?昔者齐国邻邑相望,
之音相闻,罔罟之所布,耒耨之所
,方二千余里。[4]阖四竟之
,所以立宗庙社稷,治邑屋州间乡曲者,曷尝
法圣
哉![5]然而田成子
旦杀齐君而盗其国。[6]所盗者岂独其国
?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。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,而
尧舜之安;小国
敢非,
国
敢诛,十二世有齐国。[7]则是
乃窃齐国,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
乎?
【注释】
[1]胠(qū):从旁边打开。箧(qiè):箱子。探:掏。囊:布袋。发:打开。匮:与“柜”同。摄:结,
绑。缄縢(téng):绳子。扃鐍(jiōng
jué):锁钥。[2]揭:举,负,担。趋:疾走。[3]乡:与“向”通,从。
乃:非是,难
是。积:资,用,
说当解作“积聚”。
[4]罔:与“网”同。罟:网的总称。罔罟之所布:指的面积。耒(lěi):犁。耨(nòu):锄头。
:指翻地耕种。耒耨之所
:指耕地面积。
[5]阖:。竟:与“境”通。宗庙:祭祀祖宗的地方。社:土地神。稷:五谷神。邑、屋、州、闾、乡:指各级行政单位,六尺为步,百步为亩,百亩为夫,三夫为屋,三屋为井,四井为邑,五家为比,五比为闾,五闾为族,五族为
,五
为州,五州为乡。曷:何。
[6]田成子:田恒,又称田常,齐国夫,
的先祖陈敬仲原
是陈国的公族,
逃难到齐国,受封于田,从此,陈氏
族
以田为姓。齐君:指齐简公。
[7]非:非议。诛:讨伐。十二世:从陈敬仲到齐威王,恰好经历了十二世,说“十二世”当作“世世”,
说当作“专有”。
1.上门女婿 (其他小说)
9220人在读2.神级愿望系统全领域制霸 (现代属性小说)
8961人在读3.无限之冰弓箭雨 (现代科幻灵异)
7049人在读4.鹤金游侠之洛圣都佣兵 (现代法师小说)
1526人在读5.大奉打更人 (古代至尊小说)
8382人在读6.灵境行者 (现代阳光小说)
1455人在读7.仙路美人图
3987人在读8.农家子的科举之路 (古代历史军事)
7983人在读9.苏遍全星际 (玄幻奇幻)
5176人在读10.神御之权 (现代都市情缘)
2982人在读11.剑来封天 (古代古典小说)
1103人在读12.如影逐形 (古代萌系小说)
6392人在读13.二次元之女神养成 (现代都市情缘)
1840人在读14.宏楼遗秘_基准(到91,带排校讨论) (古代)
9881人在读15.女神代行者 (现代英雄无敌)
1983人在读16.蛇血沸腾(珍藏未删全本) (现代)
2266人在读17.我能听到凶案现场的声音[刑侦] (现代复仇小说)
7216人在读18.侯龙涛
7621人在读